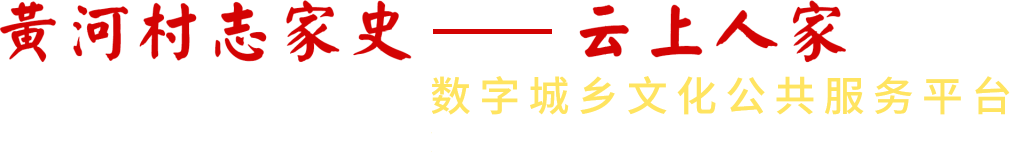前些日子在老家陪母亲小住,恰逢农历四月初八村里一年一度的古会,村委组织几个企业家出资请邵楼的民间戏班子唱了几天戏。看着扶老携幼听戏的乡邻,不由想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祠堂前筑起的土台子上,为老少爷们表演节目的岁月。
我的老家——济宁市嘉祥县马村镇张家垓村,是个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古村落。现有户籍人口四千多人,各类草根人才辈出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伊始,当时的大队党支部适应形势的需要,便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。以唱山东梆子曲调为主,伴以豫剧曲牌;既排演现代小戏,又移植排演大型革命现代样板戏,在周边十里八乡,颇有名气。每逢冬闲、过年,我们这支宣传队都要排演几出戏,年前年后持续演出六七天。有的年份,夏天晚上也演几场,助老少爷们消夏。偶尔也受邀到友好的村子去演出。我们演出的剧目有:《小保管》《下乡记》《墙头记》《姊妹易嫁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沙家浜》《红灯记》《朝阳沟》《红嫂》《白毛女》等。过年听戏是当年老少爷们的一道大菜,也吸引着周边邻村的戏迷们。汽灯一挂,锣鼓一响,家祠前的广场便人头攒动,男女老少齐盯着戏台子,跟随每个角色的喜怒哀乐互动。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春节。那个十年,虽然说外边乱哄哄的,我村却比较平静,没有派性斗争,没有宗族分歧,该种地的种地,该干啥的干啥,文化生活也比较活跃,经常有说书的、唱大鼓的、玩杂耍的、放电影的,给村民们送来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。1968年正月十五,我们村还举办了身己加工制作的焰火晚会,吸引了县城北部、汶上西部的若干个村庄的人们。那个时候我村干部作风正,群众人心齐,至今人们谈起来仍津津乐道,喜形于色。
我是在十一岁上四年级时成为宣传队员的。演的第一个角色便是现代小戏《小保管》中的小保管,一个敢于维护集体利益、与爱占小便宜的“落后分子”作斗争的少年形象,一登场,便赢得观众的喜爱。随后几年,我既扮演过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杨子荣等正面人物,还扮演过《白毛女》中的穆仁智、《红嫂》中的侯七等反派角色。这种业余演员生活持续到我上大学放寒假回家过年。1976年的春节,村里决定让宣传队在除夕、初一演出两场戏,我最后一次扮演了《白毛女》中的穆仁智。这个十年间,都是利用放假和冬闲时间排练。我还兼做报幕员,还说过相声、快板书等。我还曾在高中、大学的宣传队里演出过节目。因为演戏,我在老家一带颇有名气,至今一回来,那些健在的老婶子、老嫂子们还开我玩笑呢。那些同登台的爷们兄弟一谈及往事都感慨万千。
后来,女演员们娶的娶、嫁的嫁,男演员们当兵的、外出的、上学的各奔前程,更因为村党支部换了书记,“文革”结束政治气氛变化等原因,宣传队解散,停止了活动,道具入库,锣鼓停息,老乡们在家门口看戏,看自己人演戏的生活消失了,不久戏台子也平掉了。随着土地的承包经营,集体生活的消解,国营剧团等文化机构的改制,农村文化生活一度荒芜,戏曲没有了,说书的没有了,放电影的没有了,过的富裕的在家看电视成了唯一选择。近几年,村里的几个企业家借着古会出资请民间草台班子唱几场戏,让老少爷们重温听戏的岁月;家祠前的广场舞也跳了起来,这多少让在外工作的我有了些许欣慰。
改革开放四十五年了,乡村振兴战略也十年了,农业稳固发展,农村面貌大变,农民生活小康。村村通了水泥路,通了自来水,通了公交车,社保医保有了,网络全覆盖了……。但在农村生活,总感觉缺点什么,仔细想想,缺的就是健康的文化生活。这些年,政府也推动文化下乡,建设文化大院,街头也竖立了宣传栏等,但很多举措显然是政绩工程、面子工程,徒有虚名。深植于群众之中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形态萎缩了,如戏曲、三弦、鼓书等远离了乡村,更可叹县剧团都没了,那些为老百姓熟知的名角消失了,人们只能从广播里听听,从电视里看看,失去了扛着板凳占位子听戏的乐趣,失去了在家门口欣赏名角表演的雅兴,失去了朋友相聚听戏品戏的味道,有的只是一家人围着电视机的无奈。
我常常想,如何重建振兴乡村文化?如何培育乡村文化队伍?如何常年活跃在农村的戏台子上?诸多的问号待解!这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!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家街巷,我特别怀念那曾经灯光通明的戏台子!
(作者:张德宽 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、新闻发言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