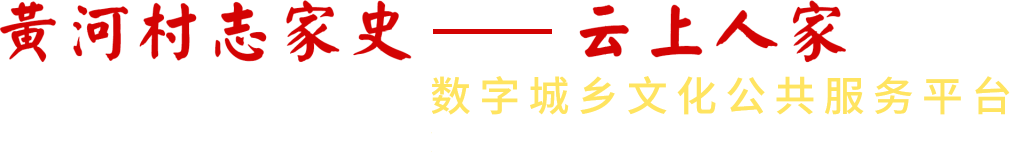几千次的弯腰,几千次的汗珠砸进黄土。那“第一次”的呼喊,是砸在晒谷场上的石头,震得人心头发麻。变迁的齿轮碾过田野,但深扎于泥土的根脉,在佝偻与挺直间传递。
(一)麦熟·光阴尺与弯下的腰
麦子,在四川丘陵的黄土地上,熟了几千次。
几千次弯腰,几千次镰刀割麦的嚓嚓声,几千次汗珠子滚下额头,砸进脚下的泥土里,洇出深色的点,又被日头烤干。几千次,麦秆被沉甸甸的穗子压得微弯,而金黄的麦穗始终直挺挺地指向天空,连成一片耀眼的锋芒,覆盖了坡地沟坎。麦熟一次,人便老一截。那金黄,是土地的底色,也是光阴淌过最深的印记。
这土地上的腰,大多时候是弯着的。像外公外婆,他们的脊梁骨,仿佛生来就带着一道与土地对话的弧度,在日复一日的耕作中,弯成了田埂边一株沉默的老树。汗珠砸进黄土,滋养着这片沉默,也滋养着一种深植于骨血的眷恋。
天地是万物的旅舍,光阴是百代的过客。人这一生,可不就是麦子熟了几十次,山花开落几十回?这便是最朴素的光阴哲学。春日埋种是盼头,夏日锄草是熬煎,秋日收割是紧巴的喜悦,冬日守囤是喘息的安稳。四季轮转,麦子的青黄轮替,早不只是庄稼活命,它成了我们丈量日头、计算年岁的尺。每一次麦熟,都是土地对汗水的回馈,是人对岁月的一次躬身。
庄子说,人生天地间,若白驹过隙,忽然而已。若以麦熟来算,人这一生,也就摊上三四十回金黄。能握住的,不过是当下这一季的风,这一晌的日头。
(二)田坝·童年印与挺直的苗
我是农民的女儿,是四川丘陵田埂上滚大的“田坝娃娃”。 我的童年,是长在地头的。
我的玩伴,是田里的泥巴。湿的,能捏成团,摔地“啪”的一声响;干的,一搓簌簌掉粉,沾满手心指甲缝。我的玩伴,是田埂边叫不出名的野花野草,春绿、夏花、秋籽、冬枯。我的玩伴,是村后小河滑溜的小鱼,是麦地豆田里窜出的灰兔。是家里灶膛边灰黄的土猫,是尾巴摇成风车的“大黄”。它们是土地给我的热闹。
我是外公外婆用红苕稀饭、玉米糊糊喂大的。爸妈很早挤上绿皮火车,去了叫“城市”的地方找活路。背影消失在村口,也带走了田埂上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光阴。
外公外婆拉扯我们三兄妹。我是老二,最“省事”。外婆挖红苕、点豆子,外公放牛、拾柴、侍弄水田。他们把我搁田埂上:“倩妹乖,莫乱跑。” 我就看蚂蚁搬家,看云变狗变山,揪狗尾巴草编兔子,或盯着泥土发呆,一坐一整天。院里的嬢嬢挑粪路过笑喊:“哟,田坝娃娃又长地头咯!” 这带着泥腥、汗味的称呼,是童年最响的标签,烫在骨头上。在他们弯下的腰背旁,我这棵小苗,懵懂地、直挺挺地生长着。
(三)远路·后座暖与归乡的辙
上学了。学校在河对岸,翻一道梁。大人脚程快,半小时。小女娃走,路长得望不到头。天麻麻亮揣个煮红苕出门,踩最后天光才见家的炊烟。冬天冷风钻骨缝,夏天晒得头皮烫汗流眼涩。脚底板磨泡,小腿肚酸胀,只想坐地不起。
后来,有了一辆半旧“二八大杠”。妈妈骑车接送我。后座上,她用旧棉袄垫好裹严,布条缠紧我俩的腰。我紧抱她,脸贴她单薄的背。土路坑洼,车子蹦跳,妈妈的背脊起伏。她头发被风吹散,扫在我脸上、脖子上,带着汗味,裹着四川夏天闷热、潮湿、混着泥土草木蒸腾的风。那味道、那触感、那颠簸的安心,刻在心上。这是父母背影缺失的童年里,为数不多烙下的、带着温度的印记。
多年后,当收割机的轰鸣代替了镰刀的嚓嚓,当黑色的胶皮管将清亮的地下水引向干渴的田垄,当年幼的“田坝娃娃”已能独自走过更远的路——当年挤上绿皮火车的那批人,我的父母,也陆续回来了。他们带回了城里的见识,沾着机油味的工具箱,存着CAD图纸的手机,和一双不再仅仅属于工地、也重新熟悉了泥土纹理的手。他们弯下的腰,曾在城市的脚手架和流水线上换取我们的温饱;如今,他们挺直的脊梁,正试图用新的方式,回馈这片曾经不得不离开的土地。科技,成了哺育故土的新乳汁,而他们,是输送这乳汁的管道。
(四)万岁·腰杆直与留白的雷
“农民万岁”的声音,第一次从村头歪脖子树高音喇叭炸出来时,我赤脚跟外公在红苕地锄草。
外公锄头顿住。他没说话,没回头。然后,我看见了——那是我从小到大见过的第一次——他慢慢地、慢慢地,直起了他那几乎与土地平行的、常年弯着的腰。浑浊的眼,望向喇叭的方向。光,在那蒙灰的眼底闪了一下,快得抓不住。随即,他低下头,更用力地锄掉一棵稗子,锄头深砸进土里,发出沉闷的“噗”声,一声,又一声。外婆在院坝簸麦,撩起围裙擦脸的手,停在了半空。
那天,外公的锄头落地的声音格外响,格外沉。外婆簸麦的动作也带着一种久违的利落。他们佝偻了一辈子的腰杆,在那个下午,似乎被什么东西短暂地、实实在在地顶直了一寸。
(五)本分·向土生与挺立的根
我永不忘记,我是农民的女儿,田坝娃娃。血脉里淌的,是丘陵泥巴色,是锄把磨破手渗出血汗的咸涩,是毒日头曝晒皮肤留下的灼热感。
田埂是我学走路的地方,也是我认识天、地、四季风、草木枯荣、虫鸟生死的地方。麦浪沙沙声,稻花淡淡甜香,红苕藤爬坡的绿意,都是刻进骨头缝的乡音。外公外婆弯下的腰,父母在城乡间奔波的足迹,都成了我挺直腰杆站在这片土地上的根基。
那粒在心底沉甸甸落下的种子,终究破土了。后来,我背起行囊,走进了四川农业大学的大门。不是农学,却也绕不开这方水土的呼吸与脉搏。在这里,我触摸书本里土壤的酸碱、作物的基因,也更深地理解了外公烟袋锅里的叹息、外婆簸箕里扬起的金黄,以及父母带回的机器轰鸣声中那份沉甸甸的期盼。书本上的字句与田垄里的记忆,在我身上交汇、碰撞、融合。
每一次麦子转黄,金穗直挺挺地缀满秆头,空气里弥漫着干燥麦香与泥土焦糊味时,就是我该记起本分的时候。这“本分”,不是勒脖的绳,是扎土里的根,是立身的气力——它连接着外公锄头下深砸的“噗”声,连接着父母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,也连接着我案头摊开的、带着油墨香的书页。
外公外婆老了。日子好了,米缸满着,菜篮子里荤素不缺。可他们依然守着那几亩地。春天点豆,夏天锄草,秋天收粮。问图啥?外婆搓着老茧:“闲着也是闲着,看着地荒了,心里头空落落的。”外公就一句:“一辈子的营生,丢不开。” 土地是他们安放一生劳碌的祭坛,根须早已与庄稼在深土里盘绕难分。他们的坚守,是我所有探寻与学习的原点。
我走到自家地头。夕阳烧红半边天,晃眼。我背对它,面朝生养我的土地。脚下泥土温热,透过鞋底熨帖脚板心。汗水顺脊梁沟流下,痒湿。
我不会低头。站得更直,像那天在红苕地里短暂挺直了腰的外公,像坡上灌足浆、穗头直指天空的麦秆。根在看不见的土里死死抓着。风来,身或晃,脚底板稳,绝不倒。用自己的力气,踩温热土地,一寸寸往上长。汗水砸进土,洇湿一小片,力气就从那湿热土里生出来。
麦子熟几千次,几千次弯腰,几千次汗滴入土。机器割倒麦子,水管引来甘泉。父母辈带着新工具归来,试图缝合城乡的裂痕。外公外婆对土地的眷恋,沉甸甸如麦粒,成为变迁中最深的锚点。而我,站在祖辈的根基与父辈的探索之上,站在书本与田垄的交汇点上。
土地在,根就在。
力气在,路就在。
一季麦倒,新种又在秋雨里埋下。一年接一年,我背对沉落的夕阳,面朝脚下温热、起伏、生养我的土地,和前方看不到头的田野,站定,站稳,迈步,往前走。
汗珠砸进土里,砸出小小的、深色的坑。
那坑里,会长出明天的力气,滋养下一季的金黄与挺直。
穗头直指天空的锋芒,正刺破更远的晨曦。
(作者:赵倩 周朝晖 四川农业大学)